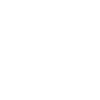18世纪,欧洲人的殖民活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塑造里,也体现在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中。许多论者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与殖民扩张进程之间的关系都有所讨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隆达·宾伯格则独辟蹊径,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少有人关注的植物。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物勘探》一书中,宾伯格探讨了欧洲殖民时期全球植物学网络中知识的转移与融合。
命名从来不是价值与政治上中立的。当时通行的林奈命名规则为新发现的植物建立了井然的秩序,却也无形中斩断了植物与其起源地之间丰富的文化关联,使得生长于亚非拉大地上的植物成为统一被欧洲人的目光凝视的对象。同时,林奈对使用植物学家的名字来给植物取名的偏好,也使得女性在植物学发展史上长期失语——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够拥有被命名殊荣的植物学家大多数都是男性。现代植物学的发展历史,自此笼罩在林奈命名法叙事的阴影下。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美】隆达·施宾格,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年11月
林奈的命名规则:
拉丁语霸权的建立
对于植物来说,命名法有意义的地方不仅在于其专业性,还在于它揭示了植物的文化史:植物和关于植物的知识在早期现代植物学网络中是如何传播的?欧洲文化如何理解植物的生物分布? 以及,欧洲植物学家如何评估其他民族的知识系统?
在某种意义上,名字体现了身份、文化定位和历史,人名自不必说,在某种程度上,植物名字亦是如此。植物被赋予欧洲名字的同时脱离了本土文化并被殖民统治所“驯化”。从金凤花的名字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历史,在苏里南的欧洲人将其称为flos pavonis 或孔雀花,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则称为tsjétti mandáru,而17 世纪的锡兰它又被称作 monarakudimbiia。 这种植物已发表过的名字纷繁复杂,多数来自东印度群岛,强调它的美丽。 到18 世纪这些名字被简化成统一的林奈科学术语,至今依然全世界通用,即Poinciana pulcherrima,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17世纪法国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岛总督菲利普·德·庞西。
林奈分类学在18世纪遭到了大量反对,准确来讲都是围绕命名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的是,林奈同时代的人在探索植物命名法时,努力将植物原产地的文化考虑进来。如果将强烈的林奈反对者法国米歇尔·阿当松的分类学作为现代分类学的起点,现代植物命名的发展之路可能大不相同。阿当松和其他人一样,竭尽全力将全球植物概念化,并且选择保留植物在其发现地的本土名字。不过林奈对此不屑一顾,抱怨阿当松的命名法说:“我所有的拉丁属名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马拉巴尔、墨西哥、巴西等地的奇怪名字,我们的舌头很难读出这些名字来”。尽管欧洲还有其他的命名法和观点,林奈命名法最终还是以其方便性取胜,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什么必不可少的需求。
米歇尔·福柯将18世纪定义为“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热衷于用新的概念框架去规训纷繁复杂的自然世界。 在这些概念框架中,名字成为专业的参考工具,仅仅是一个标签或中性的标志符,不再 具备巴洛克式的相似性概念。换句话说,名字和植物已经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按某种规范达成的共识。 著名的植物学家本杰明·杰克逊曾担任林奈协会秘书,在19 世纪80 年代负责编纂邱园植物索引。 他写道,植物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如果它和所指代的植物能准确无误地彼此对应,不会造成任何疑惑,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则无关紧要。 现在的定名者们通常也认同这点,会寻求名字的趣味性:一条化石蛇可能被戏谑地称为巨蟒;有的名字甚至可能是出资机构的代码。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不计其数的自然事物被命名者以配偶、爱人或其他人的名字命名。
这样看来,现在的名字可能抽象而武断,但命名过程并非这么随意,而是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语境、冲突和环境中产生,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追问为什么采用某种特定命名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 我主张的观点是,18 世纪发展起来的命名方式产生于特殊的文化语境之中,以著名的欧洲人尤其是植物学家 的名字为全世界的植物命名是极不寻常的现象。林奈在很长时间里都努力为这种比较新颖的命名方式辩护,在欧洲帝国主义霸权处于顶峰的20 世纪初,他的著述被作为现代植物学的起点,这种命名方式也完全被认可。 18 世纪的命名方式有助于巩固西方霸权地位,植物命名法里还融入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编撰方式,即书写了一段纪念欧洲伟大男性丰功伟绩的历史。
双名法的发明是早期现代一项伟大的成就,最初由17世纪的瑞士植物学家加斯帕尔·鲍欣提出,林奈在18世纪则将它发展成系统而完善的命名法则。双名法指的是在命名一种植物时,使用两个单词组成的名字,即属名和种加词,如Homo种植物的图匹朗博部落的叫法manyot 和其他美洲印第安叫法,如mandioque。 查尔斯·普吕尼耶1693 年在描述美洲植物时也收集和记录了植物的泰诺名字和加勒比名字;德拉肯斯坦在马拉巴尔海岸期间对采集到的植物提供了婆罗门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名字;在卡宴的皮埃尔·巴雷尔提供植物的拉丁语、法语和印第安语名字;圣多明各的普佩- 德波特则提供了拉丁语、法语和加勒比名字。
尽管很多博物学家乐于将其他大陆和文化的植物名字纳入欧洲植物学语料库,以适应快速增加的植物种类,有些博物学家却对此做法并不看好。 林奈在1737 年《植物学评论》中强调,植物学亟待发展一套严谨、标准化的“科学名称”,他的意思是要建立一套规则体系,来规范植物命名并固定下来。他将通行的做法评价为一座多语言的巴别塔。他这部200 页的《植物学评论》制定了将植物命名法标准化的规则,可以说是植物命名法的第一部法规,但这套丰富的规则删除了大量内容: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外的欧洲语言;宗教名字,尽管他允许使用从欧洲神话中衍生出来的 名字;异国名字,异国指的是对于欧洲人而言的其他国家;表示植物用途的名字;以oide 结尾的名字;由两个完整拉丁文单词组成的复合词等,这些均不可使用。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非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根的属名必须弃用”。 林奈专门针对里德·托特·德拉肯斯坦的《印度马拉巴尔花园》,宣称所有的异国名字和术语都是“野蛮的”,不过他在提到玛丽亚·梅里安关于苏里南植物的描述时,却因为某些原因觉得这些野蛮的名字总比连“名字都没有”的好。 林奈保留“野蛮名字”的条件是,可以找到其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衍生词,尽管这个词可能与植物本身或产地毫无关系。 例如与马铃薯同属于茄科的曼陀罗属,林奈允许使用这个属名是由于它与dare的关联,后者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给予,因为这种植物是拿来‘给予’那些性能力较弱或性无能的人”。

卡尔·林奈,瑞典植物学家
林奈在制定命名规则时明确地将拉丁文作为植物学的标准用语,即所有的名字和描述或鉴定都要用拉丁文发表。 “很久以前,有文化的欧洲人都将拉丁文作为常用的学习语言”,他写道,“我不反对任何民族保留他们自己的植物俗名”,“我最渴望的是所有博学的植物学家能就拉丁名字达成共识”。 实际上,林奈这么青睐拉丁文,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除了瑞典语不会其他欧洲语言,而很少有欧洲人能阅读瑞典语。 当然,拉丁语原本也是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植物学家威廉·斯特恩却认为,拉丁语被选为学者们的国际交流语言恰恰是因为很少有女性能阅读拉丁语。 斯特恩还提出拉丁语是受教育男性的专用语言,其“中立性” 有助于全球性的交流。
对其他文化来说,拉丁语并非价值中立,林奈热衷于拉丁文的 同时无非也是在排挤其他语言。他明确地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作为“植物学之父”,而不是“亚洲人或阿拉伯人”,尽管林奈认可后者古老而渊博的植物知识,但却觉得他们的语言是“野蛮的”。 植物学拉丁文在早期现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处于不断创造和翻新的过程中,各种新词被引入,其他词汇则被稳定下来,以此满足植物学家的需求。斯特恩恰如其分地将植物学拉丁文形容为应用于专门领域的现代罗马语言,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并吸纳了大量古希腊用语,主要是从18 世纪之初确立并演化而来。
“荣耀属于欧洲男性”:
植物命名中的政治
林奈意识到,什么是植物的本质特征通常可能只取决于 “观察者的双眼”而已。 现代的定名者反而会避免根据某个植物类群的本质属性去命名,因为他们选择的属性在将来可能会被证明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含糊一点可以避免今后的尴尬。林奈提出的命名法则涉及到的植物特性是抽象的,但就欧洲植物学史来讲却很具体:“出于宗教职责”,他打算“将伟大人物的名字镌刻在植物上,好让他们永载史册”。 他出乎意料地用了19页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植物学评论》中大多数词条也就1 到3 页的篇幅而已。他解释说,用人名来为植物命名历来已久,希波克拉底、塞奥弗拉斯特、迪奥斯科里季斯和普林尼等先辈们都这么做过,比他早半个世纪的前辈查尔斯·普吕尼耶和图尔内福再次复兴了这个传统。
在林奈分类学中,永载史册的人包括图尔内福、里德·托特·德拉肯斯坦、让·科默兰和卡斯帕·科默兰叔侄、斯隆和巴黎皇家植物园的安德烈·图安等。 在《植物学评论》中,总共有144 属用了著名植物学家的名字,其中50 属是普吕尼耶命名的,5 属是图尔内福命名的,还有85 属是林奈自己命名的。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没有女性的名字出现在1737年这个版本里,奇怪的是连梅里安的名字也没有,林奈其实多次引用了她的作品。只有年迈的林奈性情变得柔和时,他才用植物名称纪念了几位女性。
林奈自认为有人会反对用植物学家名字命名的做法:“如果我倡导的命名法则会引起异议的话,必然就是来自这一条了。”于是, 他从四个方面辩护了这种命名方式。 第一,将人名授予植物犹如一种仪式,可以“激发还在世的植物学家们的雄心壮志,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一种鞭策”。第二,其他学科也在用这种方式:内科医生、解剖学家、药剂师、化学家和外科医生常常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他们的发现成果,他提到了哈维的血液循环、努克管和维尔松管。 第三,这种方式与探险家的做法异曲同工,他们经常将自己的名字赋予新发现的土地。 林奈思忖道, “有多少岛屿不是欧洲到访者起的名字? 实际上,全球有1 / 4 的岛屿都以这种方式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例如阿梅里戈·韦斯普奇这样的探险家,当然不会拒绝将自己无关紧要的名字送给一个岛屿”。 他继续道,那谁又会否认一位植物学发现者的发现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用大植物学家的名字给植物命名可以将植物学史完美融入到植物命名之中:“每位植物学家都应该珍视自己传承的这段植物学历史,也要了解所有的植物学作者和他们的名字”,命名法既是历史记忆,也是向前人表达敬意,坦白地讲,植物和大植物学家用同一个名字也“省心”。
林奈在命名实践中本来也可以选择去强调其他方面,如生物地理分布和植物的文化价值。 事实上,林奈只是选择他认识的植物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以此纪念他们,这样也强化了科学由杰出个人创造的观念。就植物学而言,这些伟人指的是欧洲男性。林奈以这种方式在名称中刻画出一幅特别的历史图景,我们从中去了解世界,他的命名法重述了欧洲精英植物学的历史,也排除了植物学史的其他面向。
18世纪的博物学家热切地渴望自己的名字能被拿去命名某种植物。在准备西印度群岛之行的时候,斯隆曾写道:“有些人似乎非常渴望成为发表某种植物的第一人,而且首先要让这些植物以他们 的名字命名,但我倒宁愿我观察到的植物已经被其他人发现过”。回到英国时,斯隆发表了他1695 年在牙买加发现的植物名录,目的是做“对最初发表的作者和公众来说该做的事”。这个时期的植物学家常常机关算尽,把自己弄成第一个发表某种植物描述,并为该植物取一个恰当名字的人。 他们在植物名字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甚至在为一些特殊的植物命名时含沙射影辱骂对手。 例如,林奈就用植物学家约翰·希格斯贝克命名了一种讨厌的菊科:莶属杂草,因为后者公开批评他的性分类体系。
如上所述,现代植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有时候把命名行为描述成政治中立或无涉政治的样子。例如,1981 年《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起草者们宣称,“为一个植物类群命名不是为了体现它的特征或历史,而是为了提供一种指称它的方式,并表明它的分类位置”。但即使在21 世纪,命名法依然逃脱不了某些政治考虑,一位古生物学家曾告诉我他打算用妻子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化石, 但被同事劝阻了,最后选了一个纪念化石发现地的非洲名字,目的 是缓和在那里一起工作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关系。1905 年的命名法规依然坚持将优先权归于发表者,无疑再次凸显了欧洲受教育男性的卓越,而忽略了采集员、园艺师、信息提供者和植物学中其他默默无闻的贡献者。1905 年维也纳大会也进一步认可了林奈的选择,即将拉丁文作为植物学的学术语言,尽管美国代表抗议说这个选择“武断又无礼”,也无济于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国际会议的交流语言是法语而不是拉丁语,甚至1924 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植物学大会也是如此,直到1935 年,英语才成为这些大会的通用语言。

林奈的“药典”———既包括描述药物及其用途的印刷 品,也包括获准在药店里销售的药物。药剂师橱柜的抽屉上 都写着药物名字,有几种药物来自新大陆,如药喇叭和吐根。 一种植物要成功进入欧洲药物诊疗方案中通常需要经过当 时的标准方法测试,才能最终作为官方认可的药物,收录到 全欧洲主要城市发行的药典里。 选自《植物与帝国》内页插图,180页
林奈的竞争者:
现代植物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
林奈体系在18世纪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准确说来都是围绕命名的问题。那时候并没有人预知林奈体系会被当成现代分类学的基础,据同时代的人称,在当时植物学家“对分类方法的狂热” 的确如同“传染病”般盛行。法国的米歇尔·阿当松在1763 年曾数出了65 种不同的分类体系,他的英国同行罗伯特·桑顿在1799 年则列举了52 种分类体系。尽管林奈体系在瑞典和英国处于统治地位,但它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还没有被完全接受。如前文所言,在众多体系中,林奈体系直到1905 年才被定为现代植物学的“起点”,得到公认。
林奈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同时代的布丰,时任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 布丰反对所有分类体系的建立,尤其嘲笑林奈体系,认为它过于抽象,最重要的是太人为化。 在布丰广受欢迎的《博物志》中,他谴责各种分类体系的传播,每种体系都有一套命名方法。“恕我直言”,他继续道,“每种方法不过就是一部词典,里面的名称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反映特定的分类思想,结果不过就跟按字母顺序排列一样武断而已”。博物学家们的众多方法也是各种“充满人为想法的体系”,他强调说,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囊括整个自然界的事物。
在命名方面,布丰采用了传统的方式,将某个物种已知的所有名称都列出来,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等古人用的名字,也引用了16 世纪的康拉德·格斯纳、尤利西斯·阿尔德罗万迪、皮埃尔·贝隆等人用的名字,以及现代的约翰·雷、林奈、雅各布·克莱因和玛蒂兰·布里松等人用的名字。对布丰来说,所有“普通”的名称都同等重要,不管是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德语、波兰语、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俄语、土耳其语、“萨瓦语”、古法语还是格里森州的罗曼什语。 对新大陆的动植物来说,他则提供了印第安语、墨西哥语和巴西语名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法国人使用的名称,这些名称通常是用法语转录的美洲本土名称。
布丰反对欧洲人将异域动植物归入旧世界分类体系的做法。他警告说,南美洲有条纹的猫科动物不应该叫老虎,这种做法会让人以为在那里原本不存在的生物却被发现了。糟糕地更改、挪用、错误使用名称,或者乱起新名都会让人混淆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与新起的拉丁名相反,本土名称可以提供物种的地理分布信息的线索,例如水牛没有希腊名和罗马名,因为这种动物在旧世界不存在。如布丰指出的那样,水牛这个异国名字表明它来自其他国度。异国名称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地方动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会推测卡宴的cariacou 可能和巴西cuguacu 是同一种生物,因为它们的名字很相似。
比林奈出生晚20年的米歇尔·阿当松,也强烈批判林奈的人工体系,反对他大规模地修订植物名称,谴责他武断地改掉了植物学和医药中大部分耳熟能详的名字。阿当松谴责道,林奈要求所有生物名称都以ia、um 或us结尾,只不过揭露了林奈一味靠使用拉丁文从而让其命名法显得“充满科学气息”。阿当松与图尔内福、布丰、拉马克和法国哲学家更普遍的观点一致,反对林奈,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拒绝使用拉丁文,而是用本国的法语写作。
阿当松对林奈的挑战并非只是嘲笑对方,他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命名方式。首先,他认为要保留约定俗成的名称,尤其是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因为医生、药剂师和在田间采集草药的人等非植物学家都知道这些名字,而且在使用时可以轻易区分。因此,林奈的Mirabilis 应该恢复为药喇叭这样的名字。
对植物新种的命名,阿当松强烈建议采用任何语言的本土名字,不管是“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非洲人、美洲人还是印度人”常用的名字,只要它们不是太长即可。他在塞内加尔采集植物时,学习了沃洛夫语,并在《植物的科》中记载了大量这种语言的植物名称。由此可见,阿当松拥护的是实用的平民主义命名方法。例如,里德·托特·德拉肯斯坦《印度马拉巴尔花园》常常提供了“婆罗门”和马拉雅拉语等各种语言的植物名称,如果要在其中选一个时,阿当松会倾向于更简短、绝大多数人读起来最容易的名称。 阿当松明确批判从未走出欧洲的林奈说, “如果武断的作者们到远处旅行,他们会发现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欧洲名称才被认为是野蛮的”。对阿当松而言,在真正的自然体系确立之前,命名法都不该被固定下来,在那之前, 命名法都应该以方便简洁为原则。 阿当松兼收并蓄、去中心化的命名法,构建了人类统一性和多样性图景,他和布丰一样,都倾向于采用世界上多种语言里的植物名称。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美】范发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为什么林奈体系比阿当松的更受青睐?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癖好和制度上的政治因素对科学历史的影响。从一开始,林奈就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事业。例如,他写了一部颂扬自己的植物学史,称赞自己“为整个植物学打造了一个新的根基”。他也精心打造了自己在乌普萨拉大学的植物园和学术地位,在庞大的植物学帝国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角色。 他几乎不旅行,但他与全欧洲的博物学家都在通信,大量学生在他明确的指示下被派往美洲、非洲、印度、锡兰、爪哇、日本和澳洲等地,其中23 位最后也成了教授。林奈的儿子并没有成为父亲一样的人物,但也继承了他的衣钵,维护着他的名誉。 因此,林奈的分类法和命名法能够得到传播,可能并不是仅仅因为其本身的价值。
与林奈形成对比的是,阿当松从未获得过一个学术职位,他在法国学术圈子复杂的斗争中出局,也错失18世纪法国植物学的中心即皇家植物园的职位。因此,他几乎没什么学生和通信者。 秉承着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阿当松提出的植物命名新方法植根于更一般性的语言革新中,清除了过时的重叠字母和双元音,例如他会把nommes 改成nomes,把Theophrastus 简写成Teofraste。 阿当松这种理性化的写作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他的书没有被广泛阅读,不像布丰《博物志》那样广受欢迎。 尽管阿当松的独女也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但她和当时大部分女性一样,无法获得学术职位。
在非洲和新大陆殖民地也有反对林奈的声音。 新西班牙的西班牙克里奥尔人,如牧师植物学家何塞·拉米雷斯抱怨林奈体系掩藏了植物位置、环境和花期等关键信息,也忽视了栽培所需的土壤特征。 他进一步评论说,林奈的性体系没能抓住植物的重要特征,如用途。 在法兰西岛和卡宴工作的让- 巴蒂斯特- 克里斯托夫·菲塞- 奥布莱也支持保留植物原产地的本土名称。
18 世纪植物命名法成为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 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一种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植被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正如我们看到的,即便在18世纪的欧洲,林奈命名法也有众多的竞争者。要是阿当松的命名体系被选作植物命名法的起点,今天的命名或许会对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更加包容。但也要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有多种形式,即使阿当松也很少会关注塞内加尔人、毛里求斯人和圭亚那人如何对动物进行分类。 现在甚至很难知道还有那些本土分类法和命名体系存在,马拉巴尔海岸丰富的分类和命名实 践在里德·托特·德拉肯斯坦《印度马拉巴尔花园》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尽管依然免不了将殖民地的命名体系赶上绝路的危险,但阿当松的方法在认可全球植物学知识方面,比起林奈体系显得更加兼容并包。
剑桥大学的沃尔特斯曾指出,将林奈作为现代植物学的起点强化了现代分类学和命名体系以欧洲植物区系为重中之重的局面,林奈《植物种志》中差不多有2 / 3 的植物属原产欧洲。 据沃尔特斯称,世界上的开花植物中能让林奈可选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植物分类学的特点。沃尔特斯还特别指出,被子植物各科相对稳定,只是因为分类学家不愿意修改它们,所以不能以此认定特定类群之间的界限就必然是正确的。 威廉·斯特恩有趣地补充道,“现代科学产生于热带之外,不过它也不可能从热带产生,这种假设倒也不无道理”。 按斯特恩的说法,林奈能够建立起他的分类体系仅仅是因为在其早期的事业生涯中,他从瑞典几个教区和乌普萨拉种类少得 可怜的植物园里认得了一些植物,他并没有像后来的探险者那样, 被热带地区丰富而复杂的自然世界所折服。
换句话说,林奈的分类学和命名法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方法不过就是有机世界通用的“标准键盘”,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确立和传播时的种种偶然性,也就是说有一些天然的内在优势而已。这种情况在历史长河中时有发生:有些东西一旦被固定下来,就很难用其他方式去思考它们,以至于我们终将忘记它们原本有其他可能性。
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摘编|刘亚光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