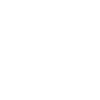香兰出嫁那年是民国十二年,婉婷收到她的信,才得知这个喜讯。
而此前她们已有五年没有联系。
两人出身不同,却很是投契,算作金兰之交。陆婉婷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她是嫡女,又生得白净可人,得尽宠爱。沈香兰的身世就要平凡寡淡得多。父亲打渔,母亲在鱼市上支一方小摊位,一家四口靠海而生。
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一段戏剧性的相遇。
陆老爷给婉婷请了先生,平日在东厢上课,那日正讲伯牙与子期的典故,婉婷忽然听到后窗上窸窣响动,她将窗户推开小缝,便看见一个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身后背了个鱼篓,篓子里装着个两三岁的男娃。女孩踩在一块并不平坦的造景石上,双手扒在窗框上,那流着鼻水的男娃够着头顶垂下来的金桔,发出窸窣声。
婉婷与正望进窗缝里的那双眼撞在一起,那么黑的一对招子,只带一瞬惊诧,毫无羞愧或是惶恐。她敏捷地跳下石头走了,甩起的麻花辫子像条乌鳢。婉婷看见,她身后还牵着两头羊。
那之后的几天,婉婷都将窗户开了小缝等她,那蹭课的人却没有来。
等她再来时,婉婷发现她换了新衣服,辫子上还绑了块花布头,身后没有鱼篓,也没有羊。
婉婷邀她进来一起听课,反正一个人干什么都是无聊至极的。那女孩子也不推辞,大大方方跟着她从东侧门进去,黑眼睛左右扫着满院的山水楼阁,只一幅镇定自若的模样。
婉婷越发觉得这女孩子有趣,像另一个世界的人,身上散发田野和天空的味道,又不像伺候她的那几个小丫头,总带着小心,处处讨好她。
后来经过婉婷请求,陆家允许香兰进出陆宅,白日里给婉婷做陪读玩伴。香兰父母起初不同意,家里的杂务要赖她做,还有一个不会走路的弟弟指望她管带,这些都是顶要紧的,读书又有什么紧要。直到香兰拿了钱回去,并说是每月都可以领,家里才放了人。
就这样,沈香兰和陆婉婷,两个本是全无交集的人,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
那一年她们都十岁。
那一年,是民国四年,女孩子仍在花园里读诗弹琴,外面的世界已经战火连天。但那些没有烧到眉睫的战火,都暂与她们无关。
那是婉婷和香兰最快活的三年,她们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婉婷和香兰分享她觉得好的所有东西,衣服首饰脂粉,或是一块她爱的点心。香兰似乎是陆宅里的又一位金贵小姐。若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日子或许会一直这样下去。
但那个夏末,香兰的父母忽然去世了。
渔家本就是危险行当,出了海,半条命都悬在帆头。可整个多风多雨的夏季都平安渡过了,偏偏在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里触了礁。那也是少有的一次,香兰母亲也歇摊跟着出海。
据说小船沉在渔民们谈之色变的鲨鱼礁旁边。十几年前有人在这礁石附近看见了鲨鱼群,不知从哪儿漂来的数十具尸体被礁石阻住,这批鲨鱼似乎是寻着气味一路跟来,围在那礁石边开始了大餐。后来人们知道,那是甲午海战里死难的士兵,而那片礁石就此便被叫做鲨鱼礁,令渔民们避之不及。大家相信,在那里落水的人会引来鲨鱼分食,必定死无全尸。
沈家的船沉在了那里,帮忙打捞的乡邻没能找到沉船,只找到沈家男人搁浅在礁石上的半截手臂。
鲨鱼礁的传说又一次被印证。而从那夜开始,沈香兰便成了孤儿。
香兰父母的葬礼是陆家出钱出力筹备的,葬礼结束后,沈家来了位极眼生的亲戚,将两个孩子带到了南方。为此邻里间还颇有了些议论——
“这是哪支的亲戚,出殡的时候不见人,这时候才出来,我看这事儿有些蹊跷。”
“谁说不蹊跷,老沈那天说了不出海,结果下午竟带着老婆出海了。他一向稳当,掌帆也是老把式,哪股邪风把他吹到鲨鱼礁上去了?还有老沈的船,死活竟找不到。”
“哪有人敢真潜下去找,还不怕被鲨鱼吃了……”
只是这些议论,随着沈家姐弟的离去也都渐渐平息。
沈香兰是当着陆老爷的面叫了那人一声舅舅的,乡亲们这才放心把这对姐弟交了出去。从此香兰便和婉婷一南一北分开,音讯不通。
没想到再一次接到香兰的消息,已是五年之后。
香兰嫁的是位黄先生,黄埔军校刚刚成立,黄先生是第一批入校受训的军官。
香兰带着黄先生从上海归宁。其实父母都已不在,所谓归宁也不过拜拜那两座空坟。
香兰带着黄先生去看婉婷时,婉婷正和几个女孩子挽着手从陆宅的大门里走出来,笑笑闹闹的一派青春活泼。婉婷歪戴着贝雷帽,短发烫了浅浅的弯,在看到那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时,她愣了好一会儿。
都已十八岁,正是璀璨的年华,若不是那封信里夹了照片,婉婷几乎要认不出她,出落得这样漂亮,浑身都散发出光,那光安静而尖锐。
“我来得不巧,你正要出门呐。”香兰先开了口,依旧是不惊不诧的一张脸,黑眼睛像是带着千斤坠,不管多稀罕的场面多大的变故多久的重逢,那眼里的千斤坠都可以镇住她的灵魂,叫她稳稳立在当地。婉婷觉得,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可以让香兰失措的。
“香兰?你回来了?写信时怎么没告诉我……”婉婷上前去,双手握住她的手,同时回头去跟那几个姑娘道歉:“真对不住,本来是你们陪我买东西,结果我却临时爽约。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沈香兰,我们多年不见了。”
那几人离开时婉婷才回身看见香兰身边的男人,二十四五的模样,英武笔挺,香兰的手挽在他臂弯里。
“这是我先生,黄继新。”香兰介绍。
“你好。”婉婷伸手和他握手,多时髦的礼节。
婉婷本是定好船票月底去英国留学的,今天约的几个女伴,便是陪她去做最后一次查漏补缺的采购。婉婷当日便把船票退了,行期推迟了半个月。香兰听着她安排,也不反对,也不客气。
晚上两人撇了黄先生睡在一个被窝。小时候香兰偶尔在陆家留宿便时常这样挤着睡,那时候两个瘦瘦小小的人儿,床却总不够大似的,让两人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如今长大了,同一张床却忽然变宽敞起来,好像中间可以躺得下许多人。
其实她们都知道,这中间隔得不单单是岁月。
“呐,小时候你最喜欢的兰花香水,你走时我想送你的,可……我没赶上给你送行,想着等再见着时送你,没想到,一等就是五年。”婉婷从枕头下摸出只青花瓷的小瓶,香兰接过来在手里摩挲,脸上若有若无的笑。
她那时候喜欢香水,因为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股鱼腥味,从发肤之间透出来,无论洗多少遍都不能消除,即使她奔跑起来,身后的风都是腥的。婉婷却说:“你叫香兰,是很香的兰花。”见了与兰花有关的物件,都会想着留给她。其中香兰最喜欢的便是兰花香水,因为她需要。她需要一个掩护层,罩在那层腥气之外。
“对了,你弟弟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弟弟他,死了。”香兰说。
“啊!”婉婷捂住嘴,“怎么……”
“偷钱,被人打死的。”这样淡淡说完,香兰又补了一句,“和我那时候一样,只是没我幸运。”
婉婷愣住。香兰刚进出陆宅没多久,就有人说看见她偷偷拿了婉婷随手放在桌上的一把零钱。婉婷不准下人再乱说,私下却跟父亲申请,每月给香兰发月俸。那以后香兰都拿和老妈子们一样的工资。婉婷是想把这件事一辈子埋在心底的,可不防被她这样波澜不惊地说破。
过了会儿婉婷才嗤地一笑,转移话题,“快说说,你和这位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他啊,不小心才会认识我。”
香兰简单说了几句便要睡去,她背对着婉婷,双手抱在胸前微微弓着身,是极无安全感的睡姿,婉婷替她掖实被子,看见她肩头露出触目惊心的疤痕,像条攀附在身后的蜈蚣。
婉婷颤抖着身子躺回去,再不能入睡。
那几日黄先生也住在陆宅里。他虽是军人,却不失文雅,对香兰体贴照护,绅士得很。
只是黄先生和香兰没住满半个月便先走了,都没赶上替婉婷送行。
回上海的火车上,香兰抽着细细的烟,乜着他道:“她比我好,是真正的大家闺秀,你后悔了吧,被我拖累上。”
“你想多了,香兰。”
“你看她的眼神我如果读不懂,这些年的繁华大上海,也算是白混了。”香兰笑了下,继续挽住他手臂,“不过我不怕,因为你逃不掉。我不想你呆下去,只是怕她知道你对她动了心思,那样我就败了。”
她千里迢迢从上海来,不过是想给婉婷看看,她过得很好,嫁了体面的人,风光无限。可若这点她自己寻到的出路也被证明并不牢靠,那这一行,还有什么意义。
“沈香兰,你真是疯了,我对你算什么,原来只是拿来向她炫耀的一件还算拿得出手的东西?”黄先生低吼。
“我不是早就疯了吗,不止让你帮我杀人时是疯的,此前很久便已是疯的。你发觉得这样迟。”香兰向他脸上吐了口烟,熏得那张英俊的脸白惨惨的。
婉婷留学三年回国。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被人流挤得站不稳脚。到处张着白旗喊着口号,她分辨了很久才弄明白,这是要打倒土豪劣绅,乡民们正涌向陆宅,她也急急地往家奔。
“别去!”一只手猛地拉住她胳膊,将她拽离人流,“陆家已经不在了,你去了于事无补。”
婉婷回头,看着一脸平静的香兰,“我爸不是劣绅。”
“有人告,那便是。陆老爷和夫人投井自尽了,你晚了一步。”
婉婷眼一黑,当即晕倒在街头,手却还死死拽在香兰袖口上。
婉婷醒来时是在一家客栈,枕边放着只信封,里面装了五百块,那几乎是笔巨款。但除此外,香兰只字未留。后来婉婷知道,的确是有人告发陆老爷。陆老爷已近花甲,却曾对家里的一个小丫头不轨;陆家的小妾又和教书先生有着苟且。如此腐朽混乱的一个封建之家。
婉婷的心重重向下沉。那些阴暗的秘密,她曾挤在床上对香兰小声倾诉,而这特殊时刻,香兰出现在陆宅附近,难道只是巧合。还是,她不告而别,只是怕被质问。
婉婷的手越捏越紧,她遥遥记起多年前那个夏末午后。
“先生的事被大约父亲发现了,父亲昨日辞了他,说正好要送我去城里读女校。我跟父亲说了,要你也一道去。”
香兰挑了挑嘴角:“去城里?我怕是没这个机会了。前几天有人来提亲,我爸妈答应了,过一阵可能就要嫁过去。那家人不会准我上学的。”
婉婷惊道:“嫁人?你才十三岁!”
香兰看了她一眼,像看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竟没有多一句的解释。
“那人……好吗?”
“大我十岁,因为有痨病,一直娶不到老婆。今年下了本钱,给了不小一笔聘金……我爸换了一艘新船。”
“我有时想,你要是没有这样的父母倒好。你若是孤儿,我一定让父亲收养你住进陆家,我们做亲姐妹……”婉婷沉默了会儿,低声道:“对不起,我这想法太无情了。”
香兰笑了:“没什么,我自己也时常这样想……”甚至祈祷过。
两人对望了一眼,手都放在怦怦直跳的心口上。那是一刹那恶意闪过留下的回音。
“今天这话可不要对旁人讲。”婉婷嘱咐。
香兰牵住她手:“你对我讲过的话,我何曾对别人说过。”
她们是有过许多秘密的,然而今日,这秘密终于成了刺向对方的一柄剑。陆婉婷迎着腊月的冷风笑了下,嘴角坚硬。
那一年她们21岁。
九一八事变后的次年二月,东北沦陷。
仍留在东北沿海的陆婉婷正和她的未婚夫许生想办法离开。离开的船一票难求。
这几年婉婷独自在家乡左近的镇里教书,许生也是那所中学的教员,并不富有,乱世中相互扶持,也便走到一起。
那日许生说是已经联系好卖家,约了时间拿票。然而去了许久不见回来,婉婷等不及,带了行李去码头等。等到的竟是最意想不到的人。
香兰穿着貂皮大衣迎风站在那里:“我是来接你的。”她手里两张船票,一张给婉婷,一张是自己的。
此时的陆婉婷也不惊不诧,她学会在变故中隐忍,在背叛中微笑,在不期而遇中掩住积蓄多年的疑问,只笑道:“这关头,也只有你还惦记着我,也只你还有本事能拉我一把。可我得跟许生一道走,他去拿票了。”
“你未婚夫?他已经坐头一班船先走了,听说是先到上海,再转到香港。卖票的说只剩一张票,如果不要,不知何时再有。”香兰顿了下,道,“他走时还是满痛苦的,心里应是有几番挣扎。”
婉婷不再问,眼底泪花闪了闪,终于被风干掉。又四年不见,但显然香兰对她的一切是密切关注的,知道她的许生,知道他们今日离开东北。所以这一张船票的离间无疑是她导演的戏,她要婉婷在她面前跌倒,然后伸出手,以施予者的姿态搭救她。
“男人嘛,怯懦自私是大多数,在这乱世,更没几个值得依靠。这样也好,你看清了他,免得将来后悔。”香兰替婉婷拿行李,婉婷也便顺从地跟她往船上走。
忽然一声喝止从身后传来,两人转身,看到三个日本兵。语言不通,但用刺刀比划出的动作却是明了的。她们被逼着上了岸。船在身后鸣起汽笛,宣告马上将要起航。
“婉婷,你还信我吗?”香兰笑着悄声问她。
婉婷也笑,只是不回答。
“我数到三,你向后跑,冲到船上便安全了。”香兰道。
“那你呢?”
“信我就不要问。”
香兰小声数到三时,码头边响起枪声。两个日本兵倒在地上,另一个退开一步拉动枪栓,香兰却迎上去,满面春风地笑。这么多年,她心底总有一个狰狞的自己,不能控制地与陆婉婷做着比较。只因为出身的不同,她就要与婉婷过着全然不同的人生,低卑、枯燥,从十三岁还未有过青春便开始禁锢在生活的琐碎里暗沉沉没有尽头?
多么不甘!
她扒在那扇窗户外,其实也并不是多渴望读书,她只想看看那窗里面得以享受这些的孩子与自己有什么不同。她看到了,于是下一次出现,她竭尽所能地让自己也干净漂亮,毫无累赘。可窗户里的人不会知道,她那一身新衣是在邻居的晾衣竿上临时“借”的,穿过了还要偷偷还回去。而弟弟被她用绳子拴在树干上,和那两头羊一起。
只这一次见面,她便用了这么多力气,下了这许多狠心。生活对于她来说,从来不平等。
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内心便越失衡得彻底。
这一生,她想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胜过陆婉婷,哪怕是借着她递出的梯子。胜过她,便是胜过了命运。所以在超越不了她时她也会将她打落下水。
而这一刻,陆婉婷被未婚夫离弃狼狈逃离的这刻,她沈香兰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她是胜利的。那么,就结束在这一刻也未尝不好。
垂在身侧的握枪的手忽然被抓住,砰,那举着长枪的日本兵脑袋上开出一朵花。握在香兰手上的那只手冰凉颤抖,然后拉着她便向船上跑,刚站甲板上站稳,踏板便被收起。
“刚才为什么跑回去?”香兰问。
“你又为什么不开枪?”婉婷的手仍在哆嗦。
香兰递给她一支烟,“还在害怕?没什么可怕的,习惯就好了。”
是的,杀人这件事,沈香兰已经习惯了。
“我那个舅舅,你还记得吧?”香兰突然说。
婉婷怔了下,听香兰笑:“我忘了,你怎么会不记得,你这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个人吧。”
“香兰,别说了。”婉婷打断她。
“难道你不想听听,那时我们姐弟在上海过得是怎样的日子?” 香兰只自顾自说下去。
那时候她和弟弟都是“舅舅”赚钱的工具,弟弟在街面乞讨,她在不远处擦皮鞋照应。那天弟弟忽然被一个男人揪住,一脚踹在地上。那男人喊:“小赤佬,贼手摸到老子身上了啊?”香兰起身,却被舅舅猛地按住,他指着自己的鞋子,往鞋面上啐了口:“别过去,继续擦。那人我们得罪不起。”
香兰抬头,看他的眼狠狠的。
“别这么瞪我,我只叫他讨钱,可没叫他偷。打死了也是活该。”
那个才七岁大的孩子被打得没了哭声,抬回去后因为不用药医治,伤口都溃烂生蛆,孩子奄奄一息地一遍遍喊着疼,她跪坐在他颜色诡异的小身体旁道:“睡一觉吧,睡着了就都不疼了。”
“姐,我犯错了。我想我要是有几张大票的话,舅舅就不会打你了……”
她闭上眼,用枕头盖在他的脸上,任小人儿扯住了她的手腕挣扎,只坚持着用力按下去。
“姐,我闷……”
“这辈子我们命贱,姐姐帮你早点解脱。”
那以后香兰本有许多机会可以逃掉,可她留了下来。一天做许多工,挨许多打,那个男人还是说过阵子要把她卖到妓院。
那时她遇到了黄继新,翩翩世家子模样,顾盼间对她有几分怜悯与觊觎。她立时抓住这块浮木,偷偷告诉黄自己是大家的小姐,被拐卖到上海,求他搭救。那日夜里,香兰给舅舅灌了几杯酒,黄继新来时,他已昏昏入睡。
黄将她掩在身后,道:“你先离开,我叫警察。”
香兰摇头,这乱世里,草芥之命怎能指望警察,否则弟弟也不会被打死街头。响动把醉酒的人吵醒,他迷蒙着眼,抓起修鞋的榔头砸将过来,彼时尚年轻的黄公子一慌,接过香兰递出的刀子便刺了出去。
那人倒下,像一条离水的鱼,腰肢跃起,似乎随时可以弹跳起来,身下的血却是汪洋,被拍打出猩红的浪花。
“快走。”黄继新拉着香兰的手。
香兰却从他手里拿过刀子,慢慢走过去,蹲在了那条鱼身边,一刀刀划开鱼腹……
那以后黄继新便收留了她,两人共有一个黑暗的秘密。这黑暗是她处心积虑抛给他的绳索,用以套牢他,供她攀爬,爬离命运。
讲完这些,婉婷的脸已是煞白。香兰背上的伤疤她不是没有看见,可她选择不问,因为问了她也便滑下了那个地狱。因这一切都是她种下的因,所结出的恶果。
“婉婷,其实他带我走那天你没有出现,我并不怪你,我知道你只是害怕。”
“不,”陆婉婷摇头,“我那时只想你离陆家越远越好,离我越远越好……”
香兰看了她一眼,笑笑地不再言语。
船靠岸后,沈香兰便昂着头离开了。在这乱世上海滩,她陆婉婷怎么求活,都是她自己的事,从此与她无关。
她们再见已经是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
香兰挽着黄先生的手,在一群军官中间交谈应酬,婉婷搂着一位港商的肩背在舞池中旋转。她们的眼神越过人群碰在一起,都是波澜不惊的微笑。
从东北撤离那日,日本兵赶来阻截,加之她那一击中的的枪法,沈香兰便知道,陆婉婷的身份不普通。而她们早晚要走到今日,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立场。
沈香兰其实没有信仰,但黄先生的官衔决定着她的位置。她们如今是政治上的敌人。可政治与她无关,她的微笑只是在说:“跳吧跳吧,我只当你是来跳舞的交际花,不会揭穿你的身份,再一次,感激我吧。”
沈香兰的胜利,都是时代给她的契机。
几十年风云变幻,经历一世变迁的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军区总医院。
沈香兰得知陆婉婷病重的消息,只身从美国飞回。
那是1976年,她们都已古稀。
病房里昏睡多日的老人听到故友的到来竟醒了过来,见到同样满头银发的来人,用褶皱拼出一朵笑来。她身上插满管子,机体似早已死去的枯木,靠着攀爬在身上的藤蔓供给营养,那藤蔓的触角抓进她皮肤探进她鼻孔。
婉婷挥挥手把儿孙们遣散,香兰坐到她床边,拉过她的手,“撑得很累吧?”
婉婷笑:“还是你最了解我。”儿孙们的孝道,只是想尽方法让她多活一些时间,却不知她的每一秒都在被死神的镰刀狠狠收割,疼痛难忍。
“我等你这么久,你不死我也就不能死,我撑得这么累,当然明白你的感受。”香兰摸她脸颊,“你要感激我,来送你这一程。”
婉婷点头:“我感激你,我一直感激你,你从来都不需要仰视我,又何必争这一辈子。”
“如果不争,或许我们早就散了……”
是的,如果不争,就不会有她一身新衣来第二次相见,以及后来的种种种种。
香兰伸手,一根根替婉婷拆掉身上的管子,婉婷安静地看着她,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夏末黄昏,香兰和她的第一次争吵。
“为什么是你?!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姐妹,和你分享所有秘密,你忘了我说过怎样痛恨那个勾引父亲的小妖精吗?可原来那人竟是你!”十三岁的婉婷哭喊。
香兰只是不吭声,脖颈笔直,眼神平静。与其嫁给未曾谋面的痨病鬼,不如选择陆老爷,这样她才能留在陆家,和婉婷一起上洋学校,见识更体面的世界,有不一样的人生。她体内有个巨大的兽,可以吞噬掉所有羞愧。
然而她们争吵的话都被香兰父母听到,朴素的渔家人认为,嫁给痨病鬼是名正言顺,给陆老爷做小却会被乡邻不齿。于是把香兰关了起来,勒令不许再去陆家,母亲甚至用她那满是鱼腥的手替她缝起了嫁妆。
几天不见她的婉婷找了来,这一次是她趴在窗口探视着屋里的香兰。
“想办法救我出去。”香兰说。
“你等我。”
婉婷没能想出什么好法子,香兰的弟弟跑出去玩了,她母亲歇了摊和父亲轮流坐在堂屋里守着,婉婷只能磨蹭着不走,直到开了午饭香兰母亲客气了两句,她也便真的留下吃饭。而后在厨房角落里瞥见黄纸包的药,毛笔字迹被潮气洇湿,大约看得出是什么“昏药”,于是慌乱抓了一把拌在香兰父母的碗里。
陆大小姐在饭桌上拄着脸等待他们昏睡过去,却等来两人口吐白沫瞬息毙命。
她惊叫着找钥匙,把香兰放了出来,来龙去脉一讲,香兰便明白了。那黄纸包上写的是“毒鼠药”,“毒”字已经分辨不出,“鼠”字看上去像一个肥大的“昏”。而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的生活里从前根本不曾出现过鼠药这样与她无关的事物,自然难以联想。
“香兰,我……”婉婷说不出抱歉,只抱着胳膊发抖,“我杀人了……”
香兰俯视着地上两具亲人尸体,静静站了会儿,然后回身去厨房,拿了把斧子。
“香兰?”
“去把门关上。”
“你要干什么?”婉婷捂住嘴。
“你听过鲨鱼礁的故事吗?”
香兰这样问时,有一滴液体溅在婉婷脸上,还是温热的。
那天晚上,婉婷目送香兰划着那艘香兰父亲新买的船出海,船舱里是两只袋子,和半截断臂。香兰在鲨鱼礁附近凿沉了那艘船,于是她的这份聘礼连同那两只装着石块和父母的袋子一起,埋进了黑沉沉的水底。石礁上只留着半截手臂,作为故事的证据。
婉婷缩在滩涂的海风里,看到那个泅游回来的黑点越来越近,在月光下一起一伏像只漂浮的头颅,耳边忽然传来脚步声,她慌忙躲起来,看见一个男人走到岸边,叉着腰等在那里,然后将已经筋疲力尽的香兰一把拽了起来。
“小姑娘,我知道你干了什么?”男人一嘴酒气,“我如果告诉大家,刚刚你的船里装着什么,你猜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香兰抹了把脸上的水,看见大石后的婉婷剧烈颤抖着,像这夜风里一只迷途的海鸟。
“你想怎么样?”香兰冷冷问。
“没什么,就是缺点酒钱。”他得到一根绳索,可以像套着小猴子一样套在这女娃娃的脖子上,往后只要拽一拽这绳子,他便可以不劳而获,“跟我走吧,去南方,那里好吃好玩多得是。”
“好,容我一天。”香兰道。
“小丫头你别耍滑头。”
“放心,我有把柄在你手上。容我回去收拾下行李,况且我还有个弟弟,明天我们姐弟俩一起,到祠堂里让你光明正大地带走,也省得乡里人追查。反正这地方我也呆不下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舅舅。”
“哦?那我得帮你收拾行李去。”男人抓着香兰的肩膀。
香兰走时又看了婉婷一眼,她抛出弟弟做赌注争取了这一夜时间,婉婷是明白的。能救她的只有陆婉婷,只有知道一切真相的陆婉婷。
可第二天的祠堂里,婉婷没有出现,她默认了香兰的牺牲,她内心里明白,让香兰带着这份秘密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从她父亲身边消失,是最好的结局。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姐妹,可以跟你分享几乎所有一切,可人是那么自私怯懦的动物,到临头才发现,原来只有一条的性命,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不会让你跟那人走,就算走,也会拉着你的手,让他把我一起带走。”病床上的陆婉婷拉住香兰的手。
“如果我也能够再选一次,我还是要这样跟你攀比一辈子纠缠一辈子。你过得好时,我便不平,心存怨念,不择手段拼命追赶;可你过得不好时,我却又想不惜一切地拉起你。为你忍辱负重,甚至可以为你舍命,却不能忍受你高高在上,一直俯视着我……这大概就是姐妹,互相爱着,也互相恨着。”香兰说完干脆地扭过头,踏上了椅子。
婉婷觉得她那一甩头的样子,好像还是多年前窗缝外面那个倔强的小女孩,一头银发,也变作灵活的乌鳢。
军区总医院里起了一阵骚乱,陆婉婷身上维持生命的导管都被拆了下来,病房中央悬挂着一具老迈的身体,那是沈香兰用那些导管自缢在屋顶的吊扇上。
两个相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在这一日同时死去。
而那些黑色的秘密,也将永远不为人知。
作者笔名:大漠芳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