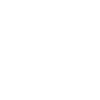梅剧《黛玉葬花》,是李蔬畦先生编写的,唱白采用《红楼梦》小说中的原词很多,尤其如旦角的“上场白”和小生“驮石碑”的大段白口,几乎全用曹雪芹的原文,不套入京剧的“水词”,旦角主曲反二黄的词句,又袭用林黛玉《葬花词》的原诗,这可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蔬畦先生告诉我:因为梅兰芳先生的白口功夫很深,无论词句怎样生拗艰涩,在他念来,总是疾徐顿挫,饶有意趣,熨贴甜润,动人心弦,不会像汤若士《临川四梦》那样“拗尽嗓子”的。所以在这出戏里,特意多用《红楼梦》原文,来发挥他的长处。
姜妙香先生的京白,是当今小生中最有功力的一位,我跟他学过《得意缘》、《闺房乐》、《马上缘》、《棋盘山》、《破洪州》、《贪欢报》、《延安关》等京白、韵白夹念的,所谓“风搅雪”一类戏;以及《贵妃醉酒》的裴力士、二本《太真外传》高力士规劝安禄山的大段“太监白”。他不但咬字真切,阴阳分明,轻重疾徐安排妥贴,其口劲深厚有力,时夹脆音,能够送到远处,此非他人所能及。所以蔬畦先生给他编上“驮石碑”的京白。

姜妙香《黛玉葬花》之贾宝玉
唱腔部分,因为此剧是梅剧新戏的早期作品,那时操琴是茹莱卿,所以唱的是传统青衣老腔,即使在40年代重演时,他也没有把后来的新腔搀和进去。梅先生认为一个戏的唱腔,应有不同于他戏唱腔的定型,如果因为某个好腔容易得彩而屡屡用之,岂不犯了内行“一道汤”的戒律?
梅先生的这个看法,我非常同意。我有几位梨园内行朋友,他们就是把一个好腔,每出戏用之,例如小生娃娃腔第二句和第四句的长腔。我曾提过意见,他们的说法是:这个腔虽是天天在唱,但观众天天不同,也许他们认为新鲜,而不会感到“熟汤气”的。我说这个想法倒是聪明,但是,天天利用这个腔,一则流于庸俗化;二则从演员着想,由于一个腔的成功,就“安于小康”,不再刻意求新、日益精进,对艺术的要求来说,这就是最禁忌的故步自封了。
而且每出戏的角色,有他特定的环境,人物性格、感情和对同台人物的烘托、陪衬等等的需求都有所不同,唱腔当然服从于所扮之角色,要各具面貌,不能千篇一律地使用。创造出符合剧情的新腔,这样才有艺术的价值。梅先生是奉行这种态度最严格的一位,值得后起学习。

梅兰芳、姜妙香之《黛玉葬花》
梅兰芳初演《黛玉葬花》,时在民国五年一月十四日白天,在北京吉祥戏园。其前有王凤卿、黄润甫的《华容道》,俞振庭、贾洪林的《连营寨》,程继仙的《探庄》。《葬花》的佐演者,是姜妙香的宝玉,姚玉芙的紫鹃,路三宝的袭人,李敬山的茗烟。这出戏以大段反调终场,全剧没有大锣大鼓,虽场上情意缠绵,而环境冷静,好像难餍众望,但舆论极好。除梅先生外,许多学梅者皆不敢效颦,畏其冷场也。
1947年复见此剧于上海中国戏院,则距其初演已30年了,兰芳与妙香均年逾50,但场上仍情切切、意绵绵、眉黛生春,毫无脂粉狼藉之憾,重新引起人们对红楼戏的爱悦。他们艺术的造诣已“入于化境”,“归于平淡”,不是以绚烂取胜于人了。
1953年初夏,姜妙香来上海大舞台演出,他告诉我说:1952年梅剧团在东北演出时期中,《黛玉葬花》演过四次,当反调唱完,帷幕慢慢下降时,台下观众被他音容所感,在如醉如痴般的良久沉浸中,才恍然大悟地鼓起掌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之后,在石家庄、天津、上海等地,这样受群众欢迎的戏,竟不再演了。大概梅氏的意思,在这个时代,演这样的戏,加上演员的年龄,好像有什么不合适似的。

梅兰芳之《黛玉葬花》
1947年,梅演《葬花》4次于上海中国戏院,我都看过。当我每次看完戏回去,总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悲感,抑塞、幽怨、郁闷,心上好似压着东西似的,沉重得很,可见梅、姜二人表演之动人,和戏剧感人之深,但这种“替古人担忧”的情绪,却是挥之不去,排遣不开,甚至把看《葬花》引为负担了。由此可见,该剧在观众中不能起到乐观的作用。解放后梅先生不因其能叫座而自动辍演,是明智的,这也是他对观众负责的地方。
但是,这出戏是梅派新戏的早期作品,它有很多成功的地方。第一,梅氏为此戏而专门设计的“古装”,为现今舞台上盛行,各剧种普遍采用。第二,当时因是梅派新腔的萌芽时期,唱腔比较质朴,可在其中找到很多传统好腔,像反二黄的“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一句,就保存着《祭塔》的〔五凤楼〕腔,可以为研究梅派唱腔者提供研究。第三,剧中夹入了《牡丹亭·游园》的“皂罗袍”、《惊梦》的“山桃红”两支昆曲的片段,虽是后台的“搭架子”,非梅氏亲唱,但可以见到梅氏提倡昆曲的苦心。舞台上也是别开生面。这些都是可以从观此剧领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