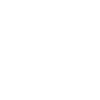玩具枪
担架是现成的,奶奶经常闹心口痛,搁猪圈楼上草旁边,马上找出来刷干净灰。一小群人抬起脚步带小跑。我也跟在大家后面得比所有人都跑得快才追得上。我拿手电筒,也有些本家亲戚打火把,幸好去小镇出了门拐右手走半里是大路也算平整,上坡、下坡、过拱桥心里都有数。好像没人路上跌过狗吃屎。公社医院的老安医生也是亲戚把全部大人都骂个遍,又接着跑,到区上有十五华里,已经是通汽车的大马路。我突然觉得奇怪,头顶有了个小小的月芽船,晃在沙砾路上,就算不打手电筒也能够模模糊糊看见东西。我一直亮着手电筒干什么呢,电筒光线又射不远,远看更像粒小金豆。我怀疑坐月芽船上的人可以看见我们像疯子在奔跑。当天晚上瘦高个年轻医生就给刘淑桃动了手术。好几个人都不动声色在看,我不敢去跟前看。
我听到窗子外有个人说了一句:
“昏死了。”
那个月芽儿船会是专门来接刘淑桃的吗?去哪里。后来杨贵珍表嫂说,她梦到了桃女,看见她笑嘻嘻走进院坝在井边用竹杆提水喝。问她什么话又不吱声。杨贵珍告诉我说,她当时就心口痛,火烧火燎的,直接痛醒过来感觉就不好。她是第二天中赶到区医院来的,刘淑桃下午4点钟才醒过来。她叫喊口渴,医生说暂时还不能喝水可以用棉纤润润嘴唇。表嫂来的时候,幺爸、大哥他们就忙着回家去了。也有人是天亮之前说家里还有事打手电筒走的。
幺爸和大哥叫我留在医院,陪杨贵珍。
许多年后刘从思住在离学校十七公里一个疗养院,所有人都是这样叫法,其实是养老医院。那是在乡下。早先我每年去看他两回,后来改成每年一次。他特别孤独。
他在一次中风后就躺在床上了。
幸亏他退休前的级别高,才有这种幸福待遇。偶尔,工作人员才会把他推出来,在花园里走走,晒晒太阳。工作人员人手不够,大多数时候板着个脸,反正不笑,但说话还是特别客气。特别是老护士长每一次她都会对我说,你家表哥看起来是不是要比上次开心点。我不觉得,话可不能这样讲,便拼命冲别人笑。这些人情绪总是会相互影响。我思忖,等到退休后,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住在这种地方的,得适应。
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东门,文昌阁斜对面,走中医学院去的那个路口。有条抹斜小岔路可以通向小河沟。我就是在那一带长大,不算轻松渡过青春期的。当年是个比较大马路菜市场,人们挤来挤去,好像黑白照片。那一年文昌阁的大铜宝顶已经被炸雷打掉了。我记得相当清楚,那天中午并没有下大雨。周围全部是东倒西歪的小栋小栋木楼、小瓦房,看不见青苔斑驳的老城墙。
叫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音连成了一大片,嗡嗡入耳。
梦中是一个黄昏。已经不是什么菜市,更不是卖小吃、衣服、小件物品夜市。这种夜市在若干年后遍布贵阳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我仿佛来到了狂欢节上。
我从哪来的,又是怎么来的?我像精神病人身上盖一床毯子,是床脏兮兮的,腥红色旧羊毛毯,带暗花纹。我又被谁怎么搁在了马路边上的。或者根本没人注意我。
有意思的,我就是直接睡在丁字街口,这让我想起拿抓傻老五来。我家好像的确有这样一床毛毯,图案更陈旧,略带黄色。父母盖了数十年,他俩去世后又传给我,说作为纪念。这时候,街灯亮起来。行道树满枝头都挂着闪烁不定的小彩灯。头顶在放烟火,这是“九大”闭幕的那天,在梦中我一直这样想来着。我张着大嘴看朵朵花儿绽放天空,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满街上的人影也都是熙熙攘攘,挤挤挨挨。粉红色的雾。笼罩恬静雾丝。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四月八节的晚上,我和汪九九在喷水池和大十字之间来回疯走。那时候夜色倒没有梦里这样凝重。我好像完全动弹不了。也有些隔得比较远的地方看上去像是满天星斗,或飞舞的蝴蝶。这样,有一艘月芽船轻松驶出了头顶蓝色天幕。
正如同离开码头驶向大海。灯光照耀在我身上。我露在外面的脸部反射冰冷光芒。
那些盛装打扮的人们有的在唱歌。我怎么听不到任何一种声音。宇宙保持着静默。
载歌载舞的队伍从我面前缓缓走过。
我并不是躺在担架上的,身体歪斜地靠着躺在一个轮椅上。就是养老院的花园中交岔小径。我身体搭着那床腥红色的毛毯。这时,有一排五个人走过来了,他们一律穿着汉服,裙边在晚风中飘动。大概距离我一丈左右,靠着我这边的三个是男的,长裙是藏青色,三人都挽着发髻,我甚至认为是哪个旧相识。但我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侧影。另外那两个女的,裙子一个粉绿,一个粉红,背上都有大朵大朵花的图案,这一排人胳膊挽着胳膊,走的狐步。
女子头发个个散披着,腰部在不停扭动。
我感觉那两个女的曾经是我的爱人,但肯定早都分手了,变成陌路。他们为什么不停下来,或者说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又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多半已经把我忘掉了。怀疑是早年间我跳芭蕾舞时那些曾经给我伴唱过的人。奇了怪,我周围全部都是轮椅。坐轮椅上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男有女。那两个女的车过头来了。她们的口红那么艳丽,刺灼眼睛,有点儿像电影上的白发魔女造型,腮红故意画得圆圆的,连鼻尖上也点了红色,有眉心。
看起来就好像一场马戏表演。
我们大家只是舞场上的小丑身份。这个人会是谁呢?看到的背影偏偏那么熟悉。
又有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参加到他们的那一排,这样差不多就把马路占完了。他们的小腿统一抬到同样高度,脚尖刀尖一样指朝一个方向。有一只脚在地上不停跳动,穿的是花鞋。大家跳的是欧洲中世纪宫庭舞蹈。我在电影上看到过的。
马路边,是一排连环画书摊。
我好像死在了轮椅上,已没有呼吸,但有意识。身体像气团那样上升在半空中。有人走了过来,揭开毛毯一角,开始对着我品头论足。先后走过来了三个人,三个穿着庸肿大袖戏服的女子,又不像吸食者那么瘦,不像站街女那么风骚或憔悴。却是水泡眼,脸像金鱼。她们都没有马上走开,更没有吓着,而是挤在一块儿喊我的名字。我记得她们的那张黑黢黢的脸颊,但我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早都忘干净了。
你怎么啦?其中一个问了句。
好像是病了。估计就快要死了。我觉得,他已经死多时了。
让我想起传说中的那种x市。
人们挤挤挨挨,推来推去,却乱中有序。难道说,他们都是一些早都死了的人。
我确实站在一个高原上,荒地。我冲对面水气弥漫着的沼泽地大喊大叫。没声音。
腥红色毛毯被哪个的手掀掉了。
毛毯上绣的花朵被一阵一阵冷风吹送,洒落在四周,花瓣让风吹开了。我从梦中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梦境。刘从思告诉我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最近,老是看到他们,就是那些死去了多年的人。我十分惊讶。噢,老表,我以为你嗓子坏掉了,原来你能够说得出话来了。他奸笑着告诉我,从前就是不想开口。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他的第二任妻子,我去过一次,家住在威西门的那个女人。他显得非常痛苦的样子,想不起来。说连她的模样都记不得了。还有杨贵珍,她死于胃癌,就是长期喊她的心口痛。我们说起了他的女儿刘淑桃,当年,她曾经给我伴唱过。我俩过家家假扮夫妻,其他那些事省略了。刘从思怀疑我说的这些事,不相信刘淑桃歌唱得好。那一年,她差点就会和谁结婚了,结果她掉进河里。他猜想女儿是自杀。
我一边和刘从思说话,一边抬起头看着他正逐渐走远。现在都快看不见他人影儿了。我忽然觉得那分明就是通往另外一个时空的隧道,出口可能有车站。下雪了,在我身边铺满雪片,白茫茫,无边无际。
我曾问过他孤独吗?刘从思摇摇头,从他的嘴里每挤出来几个字都会停顿片刻。
关于监狱的植物。太阳。月光。那些人物。病人。精神病患者。小动物。高墙。电网。独居室。刑场。可怕的电闪雷鸣和大暴雨。但是我却感觉到特别孤单。我正担心自己进了第九层梦境,已经回不去。结果,梦突然就醒了。
我出了一身虚汗,连内衣都打湿透。不知道刘从思还能够拖多久。我打算把这个梦中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说给老表刘从思听。他的皮肤苍白,细嫩。我怀疑他是长胖了,还是浮肿呢。
我并不指望他能够回答。我知道他肯定是回答不了的。
如果说刘从思死了会打电话来,他们留着我的电话号码。我在疗养院碰到了刘淑桃。她当年并没有死,传来的居然是假消息,或者,确实是有落水这件事,只不过是另有其人。乡下惯会以讹传讹。就是巧合,跟那种无脑编剧的电影故事差不离。顺水而下,也是被船夫救起。或者说刘淑桃在河边长大,她水性从小就特别好。我在那个迷宫似的花园,在交岔小径上迎面碰到了她,简直是不敢相信。
这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当真是少年时代给我伴唱的那个穿碎花红棉袄女孩吗?
在我们的脸颊,都有了老人癍,布满的是漫长岁月的幸与不幸刻痕。她推着轮椅,缓缓而行。我认出来的是靠在轮椅上的那个掉光头发,差不多连眉毛都没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