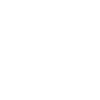听书,是以前农村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我听的是卢氏坠子书。如今已不记得说的内容了,只记得每次开头都叽叽咛咛唱一声:“小坠子一拉咱都开了腔--昂--昂--昂—昂昂,”而每次结束时,总是在紧要关头。人们憨脸掂多高,听他继续往下说时,他却戛然而止,“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
骆淑景 | 文
从前的时光缓慢而悠长,乡间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一是听书,二是看戏。
看戏需要一定的条件,最早只有大户人家才养得起戏班子,解放后县里成立了剧团,人们看戏要到县城去看。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里人为了看戏,背上被子进城排队买票。而听书,就相对简单多了。以生产队为单位,请来说书人,找个能遮风挡雨的烂窑洞或破房子就中,弦子一拉竹板一打就开始了,说个月儿四十也花不了多少钱。
记得孙玉坤来我们队说书时,就是在生产队保管窑一眼黑深黑深的窑洞里。人们用玉谷杆,或麦秸,铺在屁股底下,坐一圈圈听得如痴如醉。

我们这一带有句顺口溜,说是“瞎子打板明子唱,捏过一天是两晌”,意思是说书人里有明眼人还有盲人。说书,是上天赐给盲人的一门生存手艺。而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说书人孙玉坤,却不是盲人。
卢氏曲艺主要有锣鼓书、坠子书和三弦。锣鼓书流传于县北杜关、官道口一带的黄河流域,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坠子书流传于西南山朱阳关、五里川一带的长江流域。孙玉坤是锣鼓书的代表人物,解放前就开始说书,在卢氏、灵宝交界的福地一带走村串乡。解放后进到县文化馆,成为专职文艺工作者。
孙玉坤说书的内容随时代而变化,最早说的是《张连卖布》、《三娘教子》、《小二姐做梦》和《长坂坡》等。据说孙玉坤说《长坂坡》时,当他说道“当阳桥上,张翼德大喊一声,曹操拨转马头,人踏人死,马踏马亡”,为形容曹操人慌马乱,兵败如山倒,他用土话“扑踏踏踏踏、扑踏踏踏”,他能“扑踏”几分钟不停,真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响应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号召,他说书的内容是“小片荒,自留地,打下粮食归自己”,后来批判刘少奇,他又说唱“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坏,他把我们往邪路上带”。

姜文电影《鬼子来了》里面也有两个穿长衫的说书人,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马大三进城找杀手在城门口遇到鬼子盘查时,说书人正在粉饰太平,歌颂“大东亚共荣”;另一次是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接受日军投降时,说书人又在说歌颂抗战胜利的一套了。其实说白了,说书人就是混一碗饭吃。
孙玉坤说书有名,徒弟也多,他还收女徒弟。这女徒弟不是旁人,而是他的继女、我的堂姐。
我三叔死后,三妈嫁给说书人孙玉坤。女儿小,也带过去了。堂姐长大后就跟上继父学说书,她聪明伶俐,说书很有成就。那时特别是女人说书,更引人注目。我很小时候听说堂姐在县文化馆工作,心里就很自豪。但我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堂姐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从此不和我们来往了。堂姐的名字只比我的名字多了三撇,音也很相近。

我不记得孙玉坤说书的情景,等我长大懂事听说书的时候,听的是坠子书。卢氏坠子书的代表人物是骆小双。因为他起头总是一句“小坠子一拉”,由此推断他说的是坠子书。说这话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了,生产队请来两个说书人,一个是瞎子,一个是明子。明子老捉住瞎子的手,慢慢吞吞把他带到场地。在明亮的汽灯下,我看见那个瞎子的眼仁一翻一翻,里面都是白的。
这一次他们说的是黄公略,毛主席诗词里提到的人。毛主席诗词提到黄公略一共是两次,一次是1930年7月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另一次是1932年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里的“飞将军”也是指的黄公略。

黄公略是红3军军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早期重要领导人。说书人大概把他一生的事迹都说了吧,只记得说了有半个月时间,也没有说完。说书人先在我们队说了几天后,又到河西生产队去说。于是每到天黑,我们就撵到河西生产队去听。
河西生产队的保管院内,堆了许多木头轱辘。大家就站在木头轱辘上,仰起头听说书。那个瞎子,睁着没有瞳仁的眼睛,说的非常起劲。他手里拉着弦子,左小腿上绑着竹板,脚一抬一抬打竹板,右腿膝盖上还绑着一只小锣,说到紧要处,右手拿起小棰“梆”敲一下,和那个明子配合默契。
说的内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开头都叽叽咛咛唱一声:“小坠子一拉咱都开了腔--昂--昂--昂—昂昂,”而每次结束时,总是在紧要关头。人们憨脸掂多高,听他继续往下说时,他却戛然而止。有时候是“咚咚咚,三声鼓响,人头落地”,下面就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有时说道“忽声响,前面来了一个人。要知来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让我心里萦记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想,故事到底怎么了?到晚上慌慌张张吃过饭,碗一丢,就往河西生产队跑。但还是来晚了,没有占到好位置。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说书人,围得密不透风。有人搬来登子,站在凳子上,有人上到窗户台上,有的爬到墙头上,还有的坐到树杈上。大人把小孩子架在脖子上,把后面人影住,后面人就喊叫,“往边挪挪!”有人踩住别人脚了,被踩者就会恶恨恨骂道:“瞎子!”
有时几个年轻人恶作剧,故意挤,一挤,前面人站不住,就往后面倒。站在墙根的木头轱辘上,倒是不挤,但听不真切,也看不清说书人的表情。还有的年轻人,心思不在听书上,他们趁机在阴影处搂搂抱抱。还有的趁着人挤人,占女人便宜。摸人家一下,甚至亲一口,然后就传来一阵骂声:“恁不要脸,流氓货!”我们小孩子,过后总听说,谁谁谁和谁谁谁好了,传出许多闲话。那时没有音响,也没有扩音器,全靠说书人的两片子嘴。历史古段,筛子博篮,都在他们的说唱中活灵活现。
生产队有个瞎子文义,我爹对他说:“你也去说书吧,学一门手艺,将来老了也有个靠。”就介绍他跟孙玉坤学说书。但孙玉坤常年在外面跑,居无定所。听说孙玉坤在红石崖说书,文义就撵到红石崖;孙玉坤又跑到高堰根,文义又撵到高堰根;文义撵到高堰根,孙玉坤又跑到黑山庙。文义到底没有撵上他,那个书也到底没学成。

以说书为代表的卢氏县民间说唱艺术曾蜚声豫陕两省,但时至今日,受各种因素影响,加之一些老艺人离世,卢氏民间曲艺面临消失的危险。为抢救这一宝贵传统文化,卢氏连续举办了五届民间曲艺大赛活动。卢氏锣鼓书还成功申报为第一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这些政府行为,依然阻挡不了民间曲艺艺术的逐渐式微。
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他们是众所周知的评书大家,是人民艺术家,而低层说书人后继乏人。如今他们的后代传人都转移为“XXX唢呐队”,“XXX乐器班”,活跃在县城以及乡下民间红白喜事场所,成为一种生意,完全走了味儿。
作者简介:骆淑景,女,六十年代生人,现居三门峡市卢氏县;喜爱文史,笔耕不辍,著有多部长、短篇作品。
本期
编辑:云济
豫记版权作品,如需转载,请微博私信“豫记”或发邮件至yujimedia@163.com
豫记,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