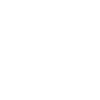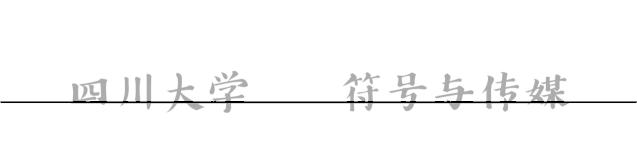

作者 | 余韬 吴思捷
摘要
传统的符号学关注文本,观众由电影建构,陈述过程内在于文本,文本建构中“语境”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罗杰·奥丹的符号语用学(Semio-Pragmatics)则是一门旨在研究影片生产与接受过程的学科,它不仅仅关注文本意义的建构,还强调文本之外的空间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对我们理解意义带来的改变。语用的立场使得符号学家能从更广泛的生产流通实践中考察人与物或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而落回到对文本的阐释中,它综合了结构语言学与认知语用学的方法和路径。本文从观众、空间、体制和模式等领域分析了奥丹语用学核心概念与传统符号学的关系。他的研究为符号领域提供了一个解释模型或策略,开辟了一条重新理解观众的路径。如同一把扫除蒙蔽在研究者精神意识上灰尘的扫帚,让当今的影片分析或电影研究拥有了新的立场和角度,去理解作为物的媒介技术和作为人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今天的电影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罗杰·奥丹;符号语用学;电影符号学;语境
罗杰·奥丹(Roger Odin)是巴黎第三大学(Paris 3 University)传播学荣誉教授,于1983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该校电影与视听研究院(Filmand Audiovisual Institute)院长。他代表了麦茨(Christian Metz)之后法国电影符号学的语用学研究方向“:在法国,这主要靠罗杰·奥丹,他从事建立电影符号语用学已有多年历史”,在其带领下,奥丹及其小组展开了对纪录片、家庭电影和业余制作电影的研究。在新方法的指引下,奥丹等人不是只关注于文本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还在更广泛的生产与接受环境中考察意义的问题,也正应和着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大方向,即强调在现实运作中找到各式各样的文本建构和意义生成的模式。通过将符号学与语用学的结合,罗杰·奥丹的研究方法具有一种内在的创新意识和生命力,也正因其建基于技术媒介与电影的语用交际视域,近年来奥丹越来越关注于移动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前景,并着重思考手机—电影的制作及播映空间,尝试在传统的观影经验“四分五裂”的当下重建起电影理论与新环境的关系。这一创新让奥丹得到了英美学界的重视,并对其展开了积极有益的引介,如沃伦·巴克兰德(Warren Buckland)所著的《电影认知符号学》(The Cognitive Semiotics of Film,本书亦有中文版)便有对奥丹语用学中几个关键概念的详解,奥丹针对新技术的研究成果也被广泛翻译成英文版。国内目前对奥丹的了解和译介并不丰富,王国卿翻译的《什么是符号语用学》(Se?mio-pragmatique)便是其他学者为奥丹理论所写的简略引论,而奥丹自己所写的几篇文章虽被翻译成中文,却与符号语用学的理论本身关系不大(如《语法模式、语言学模式及电影语言的研究》《作为教学练习的影片分析》),而该理论和当下互联网新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未能获得高度重视。笔者在本文中希望通过对奥丹理论的系统性梳理,勾勒出符号语用学的核心基础及其相关概念原则,详述奥丹在其理论中勾连影片及其外部的技术和生产流通环节,从而改变对文本意义的建构;同时也要注意奥丹在语用的立场下,对文本诠释的经典命题所进行的重构,进而能指引我们在“新符号学”的思维下打破固有的偏见,使之成为批评与解释策略的独特路径(Approach)。
1 虚构化的观众与“具体”的观众:从麦茨到奥丹
在电影符号学的第一个阶段,麦茨区分了影像与自然语言,并以此为基础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融入了电影研究理论,服务于影片文本的分析。他提出了影片整体的大组合段模式,并利用耶尔姆斯列夫(Louis Trolle Hjelmslev)的表达/内容阵列确定电影的特殊/非特殊符码。麦茨总结道:“电影语法概念如今备受批评;因此,它似乎已不存在。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准靶向......单有形象的模拟,说明不了影片表述中各种并列现象何以不难理解。那是大语意段系统的任务。”麦茨指明符号学的任务是理解影片得以被理解的基础,并认为这是“大语意段系统的任务”,也就是一套存在于或共享于导演—观众之间的独立客体——符码。
然而一旦触及理解的过程,就无法忽视观众主体的存在。理论自身也必须为观众的心理或心智结构假设一套认识的过程或方法。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就从认知主义立场提出了一套图模理论(Schemata),解释观众如何运用先在于大脑中的知识背景来辨识叙事及的风格。所以在麦茨转向精神分析的研究过程中,其路径暗示着他不再认为符码是影片接受和理解的唯一基础,并考虑到了观众作为主体的能动接受与建构作用,他在《历史和话语:两种窥视癖论》(Story/Discourse:A Note on Two Kinds of Voyeurism)一文中说道:“我在观看电影时正在帮助它出生,我在帮助它生存,因为它正是要生存于我心中,其制作的目的正为此:被看,即在被看时才开始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麦茨的初级与次级认同才借鉴并改造了拉康的想象—象征概念,以此假设了观众与摄影机、影片人物、分镜结构等的多元网络关系。
“当观众作为视点与自己认同时,他只能同摄影机认同......至于与人物的认同,与他们本身的不同层面的认同,都是次级和三级的电影认同。”麦茨所描述的这一过程,与其说是观众主体帮助影片“出生”,不如说是观众从真实的物理环境进入了虚构的影片内环境的全过程,这里当然还包括封闭幽暗的影院、被限制的行动、被突出的视觉感知等。观众成为虚构化和理想意义上的普遍主体,认同也是观众所拥有的一般能力。
然而这种对认同机制的理解牵涉到的是怎样的认同?“我”的具体身份为何?此种身份所带来的对具体影片的态度有何差异?这种态度又如何最终影响“我”观看并理解影片?影片是否会调整“我”的先在身份和认识(指观影前就具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在麦茨的论述中,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一般化的接受过程不仅遮蔽了观众的身份差异,还掩盖了影片繁多的种类对接受带来的改变。观看一部西部片和一部歌舞片,观众最初所具有的期待视野和心理结构可能就不完全相同;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处于当代的观众回看过去的影片也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问题意识,这些心理条件也会影响对具体作品的判断和理解。正是在面对这些“后现代”的去中心、多元化的问题下,罗杰·奥丹对麦茨的重读才引导他发展出一套基于语用立场的符号学。
在奥丹的理论视野下,“交际是所有主体积极参与的活动,他们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说话人还是听话人),在互动的过程中都平均分工......交际主体共同构建意义”。语用学不仅认为话语的内容意义在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形成,还进一步肯定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在具体的交际行为中得以建构的(而不是事先给定)。在奥丹看来,导演—观众的角色只是一种行动元(Actant)建构,我们并非被强迫承担类似的角色,“行动元导演和行动元阅读者绝没有先验的理由会承担相同的角色(相同的形成意义和产生影响的方式)”。相同的角色意味着“我”和“你”拥有同等的意义生产和解读的方式,语用学强调的是在交际过程中形成(而非给定)的角色位置,这不仅颠覆了结构主义者关于符码共享的信念,同时也让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濒临瓦解。个体既有的身份并不会使他/她自动成为行动元观众(或阅读者),只有在交际行为达成共识的基础下,观众的心理结构才会对应于影片的生产及文本结构。为此,奥丹提出了交际空间(Communication Space)、模式(Modes)、体制(Institution)等概念,用以建构导演—观众行动元之间的交际行为理论模式。
实际上,在历史的发展中,观影行为的发生空间早已从影院延伸至了客厅、卧室、手心,客体也早已从银幕延伸至了电视机、电脑和智能便携设备,单纯的视觉也与触觉相连,传统的理论已不再能面对崭新的在人机互动环境下的观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说:从麦茨到奥丹,便是从虚构化的观众走向“具体”的观众。“奥丹的方案就使多样的电影风格连同它们的外部限制一起产生了多样的心理状态,或注意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符号语用学并非对真实观众做量化调查和研究,这里所说的具体,是根据不同的风格样式而采用的不同阅读能力,即“体制为了自己能够运转而要求的(也只有在放映时才要求的)一种能力”。
2 交际空间与体制: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动
语用学要考虑的是真实对话中两个和两个以上主体间的关系及由他们所处时空所形成的环境。当奥丹试图将这一理论立场沿用至电影研究领域时,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处于接受环境中的观众并不直接面对创作话语的导演,而是面对正在放映的影片信息流。“电影能够表现某种时间和空间关系,但只能是复指性的,即只能表现它自身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时空关系,而不是电影和其他的某个人和某件事之间的时空关系”,“陈述是一项符号化行为,通过这一行为,文本的某些部分向我们谈论作为行动的文本”,麦茨将影片看作是封闭自足的文本,而不与外在的某人或某事发生关联。当我们将交流限定在人与人之间时,这一判断是对的;但若交流是指发生在人与物之间,以及人通过物间接地与他人交流时,麦茨对影片的理解会显得很可疑了。
如果把物的概念定位在媒介技术之上,这一技术就具体指向了影片以及制作影片和放映影片的机器。罗杰·奥丹用装置(Dispositifs)来描述它,这就去掉了它作为现代科技物的意涵,而成为人与物之间交流的装置物。“在我使用它的意义上,装置是一个有意向的‘操作者’,一个由一组组件(通常是技术性的)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连接在一起的结构,包括使用者,并让使用者服从于一种被精确决定的行为类型(and Subjecting Them to a Well-defined Type of Behavior)。”所谓使用者即是与装置互动的个体,如“坟墓就是一个装置,其中包括墓碑、雕像、碑文等等,而我们则被邀请进入这一空间中,展开悼念死者的行为”。在奥丹随后的描述中,装置与空间密不可分,那些机器性质的物总是被组织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之中,以形成具体的网络结构。在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体系内,它们共同形成了“媒介”。“这些工具变成机器,它们是由技术系统构成的,而这些技术系统本身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宏观技术体系’。”这一发展过程可以被简述如下:文字和纸张用以记载保存数据或记忆,档案馆与图书馆便拓展成具体的储存建筑和组织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变成了比特数据,图书馆变成了互联网软硬件的储存等。奥丹也依据这一整个配套机制提出了交际空间(Communication Space)的概念,这一空间不仅仅由技术组成,也由因技术和媒介而改变了的背后的产品生产组织和结构组成,以及技术和媒介所决定的产品接受的环境和空间组成。所以,接受者和接受行为、环境与方式,生产者与生产行为、组织与结构(文本结构),以及媒介技术本身,共同构成了我们处于其中的交际空间。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电影交际空间、家庭交际空间、电视交际空间、网络交际空间、档案馆交际空间等。随着技术的变更,生产与接受行为会随之变化,因而这一交际空间的序列也并非固定的,奥丹在后来的研究中针对新技术就提出了电影—电话的空间,用以表示我们在手机上观影时的情境,并细化处理了各种不同的认知及注意模式。
交际空间概念的提出让奥丹与麦茨在关于文本的立场上背道而驰,从后者的陈述理论出发,观众对影片的解读将导向一种不确定性,即影片“只能表现它自身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时空关系”而与外在的生产/接受环境无涉。奥丹的概念则在一定意义上约束了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行为:“在这个交际空间中,种种限制使得行动元(发送者和接收者)共享相同的体验。这一系列的约束制约着行动元角色的构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意义和情感的产生方式的选择。”这一限制被奥丹用体制一词来形容,这个词也就回到了先前所说的生产与接受的整个配套机构,但同时也包含着更广泛的时空。比如在分析家庭电影时,奥丹就创造了家庭体制(Family Institution)的存在,这一体制使得不同行动元之间被一种关联轴(Axis of Relevance)所限制,“这是我所使用的(家庭)关联轴:通过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建立联系,记忆是确保家庭单位内部凝聚力的元素”。家庭往往就是这样一种纽带,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记忆和精神的空间。通过照片、仪式、肖像画、珠宝、信件、明信片等内容,将逝者与生者联系在一起。而基于家庭电影是由家庭内成员(通常是父亲)制作,所以所拍摄对象往往是重大纪念日(子辈出生、结婚纪念、节假日游玩等),并且缺乏背景交代和事件之间的关联,对于家庭外成员来说就只能面对一堆碎片化的影像,而内部成员却总能由不同的片段勾起相似的记忆。家庭体制(种种在先的常规)—家庭交际空间(生产与接受的组织逻辑和技术)—家庭电影(装置)—家庭内的行动元,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组成了一套特定的“生产—阅读”方式。
影片的生产与流通环节受到了多重限制,这些限制又仿佛铭文一样在最终的文本结构上印刻着自己的痕迹,它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观众对它的理解,正如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所说,“它能使再现客体以作品的本身事先确定的方式明见地展现出来”。奥丹的语用学当然没有抛弃符号学的组合/聚类双轴分析法,但他更强调文本结构或意义之外的那个“空间”,而作品本身也将会广泛地牵涉到政治经济的环境当中,并联系起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产生有益的理论对话。
3 模式与空间的混成:多元交叉的交际互动
通过将文本与其外的生产接受空间联系之后,奥丹向我们提供了“观看电影”的新模式。但体制的概念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即它似乎等同于某种“大结构”,并决定着我们对电影的接受模式。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讨论的,体制与交际空间不仅仅具有外在物理的形式,它们还会内化为观众行动元或真实个体的心理—精神形式,并形成我们的认知能力,“为了解释在不同的交流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似乎有必要增加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这个概念存在于我们脑海中,却很可能是从“外部”获得的,奥丹举了电影心理空间的例子:虽然我们不是时时刻刻处于电影院中观影,但这一经验却是时时都有的,大银幕、黑暗的环境、高解析画面和高保真音响等,它们成了铭刻在我们心灵上的痕迹。当用手机看电影时就会不同程度地感到异样,而有一些用于电视播放的电影也会模仿我们进入电影院的体验。但心理空间更包括一个人的身份历史特征,如信教者就区别于无神论者,这些先在的理解就会影响它们的接受。体制则与观众对电影语言的习得有关,奥丹认为在移动设备普及的今天,电影语言与我们的日常交际环境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需要用到视频通话、直播等的情况中,“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实情,这些创造此类镜头的人,已经整合了(至少隐含地)电影语言的形象”。
在人与技术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奥丹认为我们逐渐习得了一种外在于我们的能力——通过镜头或镜头组合叙事。当奥丹提出多种电影模式时,他的目的并不是做出一种文体学的划分(从文本结构的特定句法风格总结出不同种类的文本),相反,电影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导演/观众的心灵中,是互相交织的认知能力,而非类型概念那样的严格划分。从理论上来说,观众可以用同一种阅读模式观看不同生产模式制作的电影,也可以用不同的阅读模式看同一部电影。但实际上,由于受到了关联轴和体制的限制,观众总是会优先选择与语境关联最强,且加工信息付出最少努力的模式。为了在不同的阅读模式中进行切换,观众需要进行一定的意向性改变,以此注意到先前注意不到的部分。在《家庭电影文献化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Family Home Movie as Document)一文中,奥丹从如何将家庭电影看作文档或纪录电影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它对时代和社会的广泛作用。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众多不同的家庭电影都是重复同样的内容,这就削弱了它的信息价值;家庭电影并不引发我们对真实性的思考,相反它将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家庭电影只有欢乐却没有痛苦,它审查排除了太多“真实”。为此,奥丹提供了多种对文本进行“颠覆”的策略,他注意到家庭电影纪录的都是琐事和平凡之事,这一切都是电视台或专业纪录片工作者不会记录的内容,于是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逆向阅读的政治意义:“家庭电影有时是被官方历史边缘化的一些种族、民族、文化、社会群体的唯一记录。”这对于那些社会政治混乱,无法找到民族认同的地区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创建家庭电影档案馆,能有效帮助凝聚起当地社群。“这种类型的档案通常发生在存在民族认同问题的地方(布列塔尼、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苏格兰等)。”
通过调整我们与电影之间的“位置”关系,先前决定我们的体制或交际空间,也会反过来被我们创造,从而或可以生产出新的关系与意义。奥丹的语用学也因此带上了认知语言学的色彩,“当阅读的历史背景发生变化时,一部不太重要的电影会突然变成一部绝妙的文献”。奥丹在此处所说的背景变化,也就是“框架转变”(Shifting of Frame)。框架语义学认为一个特定社会共享特定的认知域或框架网络,对其中一个含义的辨认总要连带出背后具体的知识背景,“一个似乎正确的判断是,在定义和理解词义时所参照的框架大部分属于我们所处的文化”,当框架转变时,词义也就会萌生新意(英文中的Bachelor在海狗群落框架中就被表达为无伴侣的雄性海狗),这也是隐喻得以产生的基础。但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观众有能力在不同的交际空间或体制内进行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将改变研究者与影片的关系,如果从历史考古的角度出发,旧时代的故事片或可成为对人文社会风情的考据式观察;而对于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事先固定的类型或文体学划分,则很可能就会面临着“瓦解”与“延异”。
4 从理解观众到分析实践
罗杰·奥丹的语用学立场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对观众理解影片过程的阐释。这无疑继承自麦茨的符号学传统,然而我们仍然只能说这是一种基于多种前提的假说,而不能就此断言语用学就完全地解释了观众的心理过程。基于交际立场的相关性原则就已经被心智模型理论“证伪”。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奥丹的语用学还是为电影研究和批评带来了崭新的范式变化。笔者认为这一意义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语用学颠覆了影片文本与分析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请我们注意到影片背后的媒介技术,以及技术生产的整个组织逻辑与制度框架,还有它们在具体接受空间中的接受情况与效用。如奥丹对于媒介新技术的观察,使得他关注手机—电影的新领域,以理论的姿态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
其二,多种模式虽然不一定是具体观众具有的认知能力,但它也为分析带来了便利和好处,尤其是这些模式之间可以随时互相切换。如果从模式这一概念迁移到风格与类型当中,即后者也是一种存乎于导演—观众心中的认知能力,无疑便从另类的角度对传统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一部影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是表现主义、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导演能否在整体上协调起不同的风格类型?而在充满了迷影情结、多元互涉、致敬、戏仿的艺术生产实践中,该如何看待类型的拼贴与混成?
其三,在数字媒体技术的今天,研究界正在重新思考影像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然而奥丹的语用交际立场却从话语陈述命题中,对待诸如动画纪录片等新兴现象。奥丹的概念里有一项名为虚构化的操作,这是指陈述者是否为真实/虚构,陈述者为真,影片即采取纪录片风格。所谓陈述者为真,意味着摄影机/摄像机/镜头背后具有一个真实的“说话人”或者机构,他直接参与并向我们显现于影片现场,从而对我们提出关于事件真实性的问题,引起我们对影片世界的严肃思考(易言之,这是一种自反性)。相反的,虚构的陈述者则隐匿其身形,或者将电影机制隐匿在故事世界中,也即是麦茨所谓的“故事”。语用学无疑摆脱了对影像物质性和真实性的追问,转而从话语类型的角度研究真实/虚构。但若我们如奥丹一样采用他的语用立场,承认意义是从交际互动中形成而非事先给定,就能从影像与事件的真实与否、陈述者的真实与否等多维网格中确定一部影片的“操作”。作为结果而言,影片的真实性或可以游走在异常模糊的境地。除了动画纪录片的真实(真实事件/采访对象)采用虚构(说话人和影像的虚拟)的立场之外,还有诸如《探访惊魂》(The Visit,2014)这一类影片,是虚构(故事,人物)采用真实(说话人)的策略。
奥丹的研究并非完美地给出了一个解释模型或策略,但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基于认知和语用角度的新符号学对于今天的电影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仅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观众的机会,还是一把扫除蒙蔽在研究者精神意识上灰尘的扫帚,让当今的影片分析或电影研究采取全新的立场和角度,去理解作为物的媒介技术和作为人的我们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Roger Odin,Reflections on the Family Home Movie as Document.Karen L. Ishizuka & Patricia R. Zimmermann,Mining the Home Movi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255.
(法)雅·凯玛邦著.王国卿译.什么是符号语用学.世界电影,1990(1):27.
关于罗杰·奥丹的出版书籍,详见:Roger Odin,Cine?ma et Production de Sens.Armand Colin,1990.Roger Odin,De la Fiction.De Boeck,2000.RogerOdin,Le Film de Famille.ME?RIDIENS-KLINCKSIECK,1995.Roger Odin,Te?le?phone Mobile et Cre?ation,in Collaboration with L. Allard et L. Creton.Armand Colin,2014.
奥丹的符号语用学文章被收录在下列英文著作中,详:Ed. Susan Aasman,Andreas Fickers & Joseph Wachelder, Materializing Memories: Dispositifs,Generations,Amateurs.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 BillNichols & Michael Renov,Cinema’s Alchemist.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Ed. Laura Rascaroli, Gwenda Young & Barry Monahan,Amateur Filmmaking:The Home Movie, the Archive ,the Web.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4.
克里斯蒂安·麦茨著.崔君衍译.电影表意泛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
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著.李显立等译.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台北:远流出版社,1999:82.
克里斯蒂安·麦茨著.李幼蒸译.历史和话语:两种窥视癖论.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249.
克里斯蒂安·麦茨著.王志敏译.想象的能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46-52.
布鲁诺·G.巴拉(Bruno.G.Barra)著.范振强,邱辉译.认知语用学:交际的心智过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2.
(英)沃伦·巴克兰德(Warren Buckland)著.雍青译.电影认知符号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7.
沃伦·巴克兰德著.雍青译.电影认知符号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5.
雅·凯玛邦著.王国卿译.什么是符号语用学.世界电影,1990(1):27.
Christian Metz,Impersonal Enunciation, or the Place of Fil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146-148.
Roger Odin,Amateur Technologies of Memory, Dispositifs, and Communication Spaces.Susan Aasman, Andreas Fickers & Joseph Wachelder, Materializing Memories:Dispositifs, Generations, Amateurs.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20.
(法)雷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y)著.刘文玲,陈卫星译.媒介学引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1.
Roger Odin, Spectator, Film and the Mobile Phone.Ian Christie. Audiences.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3:155.
Roger Odin, The Home Movie and Space of Communication.Laura Rascaroli,Gwenda Young & Barry Monahan, Amateur Filmmaking: The Home Movie, the Archive, the Web.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4:15.
(波兰)罗曼·英伽登(RomanIngarden)著.张振辉译.论文学作品.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71.
Roger Odin,Religion and Communication Spaces. A Semio-pragmatic Approach.www.jrfm.eu,2015(1):23-30.
Roger Odin, The Single Shot, Narr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he Spaceof Everyday Communication.Ian Christie & Annie van den Oever ,Stories.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8:167.
电影模式最早只有八种:奇观、虚构、动力、家庭、纪录、艺术、教化、美学。但在随后的进展中,奥丹又发展出了制作模式和私人模式等等,这些概念本身并非泾渭分明。可参考(:英)沃伦·巴克兰德著.雍青译.电影认知符号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12:82-83.
该原则出自斯珀波(Dan Sperber)和威尔逊(Deirdre Wilson)的相关性原则(PrincipleofRelevance),可参考(:意)布鲁诺·G.巴拉著.范振强,邱辉译.认知语用学:交际的心智过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6.
Roger Odin,Reflections on the Family Home Movie as Document.Karen L. Ishizuka & Patricia R. Zimmermann, Mining the Home Movi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263.
Roger Odin, How to Make History Perceptible.Bill Nichols & Michael Renov, Cinema’s Alchemi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2011:138.
Roger Odin, Reflections on the Family Home Movie as Document. Karen L. Ishizuka & Patricia R. Zimmermann, Mining the Home Movi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2007:262.
(比利时)德克·盖拉茨(DirkGeeraerts)编.邵军航,杨波译.认知语言学基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20.
(意)布鲁诺·G.巴拉著.范振强,邱辉译.认知语用学:交际的心智过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7.
存在有其他六种操作:赋形化,剧情化、叙事化、演示、信念、定相、虚构化。可参考(:英)沃伦·巴克兰德著.雍青译.电影认知符号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5.

本文刊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编辑︱黄思睿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